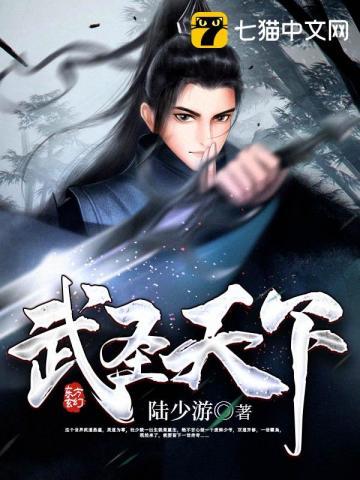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六十五章 暗室之灯(第3页)
原像实验室没有名字,没有门牌,也没有日常行政结构。
甚至连办公时间也没有明确规定,五个成员几乎都按照自己的节奏来,每天进门第一句话不是“你好”
,而是“你今天还相信你自己吗?”
这听上去像是一句玩笑,但他们都知道,秦川早就不是在做一个面向现实世界的系统了。
他现在做的,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剥离与重构。
“我们现在不再需要别人的理解。”
某天深夜,江允来访,站在原像实验室门口,看着这幢灰白色的老楼,“但你还需要你自己的解释。”
她看着秦川,眼神里没有责备,只有一种几近悲悯的沉静。
秦川沉默良久,只说了一句:
“我不是想变成另一个神,我只是想看清人是不是还需要神。”
原像的研究,不再对外公布进展,但它所引发的社会余震却开始在“行为系统”
的边缘蔓延。
灰域在结构上仍然保持高速增长,甚至已经成为南方多个城市政务运行的默认底层架构,但它的“话语权中心”
已经失去了统一性。
很多人开始追问:
“秦川去哪了?”
“他为什么不再发声了?”
“他是不是退出了?”
可真相是——他没有退出,而是潜入了更深的层面。
那天晚上,五位原像成员围坐在桌边,面前没有文件,没有程序,只有一盏台灯,一本厚重的手写本,一支接一支写下的问题。
问题被归档为“暗室结构组”
。
即——在完全黑暗、无人回应、无法验证的前提下,一个人是否仍有自我认知的可能?
秦川说:“原象的核心不是系统,是秩序的虚空。
我要找的,是那个虚空里,仍然有光的逻辑。”
有人说这是精神结构的自残实验,但秦川坚持称之为“认知的脱依附训练”
。
“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孤独中生出秩序,他就无法在秩序中保留自己。”
于是他们开始进行一系列极端的模拟——
不记录、不过问、不过审、不能评估、不能对照。
他们创造一个完全不提供反馈的逻辑模拟房间,在那个房间里,一段程序被投入运行,没有人知道它运行什么,也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停下。
唯一的评估标准是:这个程序是否会主动选择继续。
他们将这段程序命名为“暗室灯芯”
。
三周后,那个程序没有崩溃,也没有停止,而是在第二十二天主动重构了自身逻辑,试图生成“运行原因”
- 婚后心动:凌总追妻有点甜金秋
- 只有鱼知道水陆青栖
- 镇国南帅治肾亏不含糖
- 天师下山,总裁老婆请自重虎帅
- 仙子的修行·美人篇yehou123
- 端庄美艳教师妈妈的沉沦无绿修改版佚名
- 妙手龙医金佛
- 雪意昭昭七颗荔枝
- 神雕欲女晨月
- 四合院之啪啪成首富雨是苍天在哭泣
- 凌云天途风和暖阳
- 无限之禽兽修仙者(修仙少年的艳途)三年又三年
- 美母的诱惑大唐妖僧
- 美母如烟,全球首富佚名
- 村里的留守女人之少妇夏月汉武秦皇
- 至尊鼎老狐
- 癌症晚期,前任女友疯狂报复我半城清梦
- 嫁督主锦一
- 官途危情巴山破晓
- 四方极爱Howlsairy
- 前夫哥他老实本分夏西泽
- 官道升天魔礼红
- 官场之美人为陷春歌本尊
- 魔道祖师墨香铜臭
- 水浒揭秘:高衙内与林娘子不为人知的故事(贞芸劫)xtjxtj
- 邪恶小正太的熟女征服之旅疯狂的笨笨
- 溺爱儿子的爆乳肥臀教师艳母,竟然是头痴女母猪(无绿修改版)琴师
- 美妇厨房(纯爱加料版)kasya10
- 美母的诱惑大唐妖僧
- 色气妈妈诱惑初中生儿子一之麻
- 贯穿绿母癖男孩青春期的风骚熟母乱交史云茗的二号机
- 被黑人用外星人科技洗脑改造恶堕的居间惠和丽娜愛と税のために
- 肥宅肏穿斗罗大陆清酒
- 父债子偿拉大车的小马
- 我的美母教师纳兰公瑾狼太郎
- 因为爱所以乱(玩弄母亲)佚名
- 重生之娱乐圈大导演开飞机抓仙女
- 高中三年,我让陪读母亲陪我上床两面三刀
- 巨根正太勇者的母猪后宫AD
- 催眠之御姐熟妇让我操(控制)华风
- 重生少年猎美三年又三年
- 美母的信念大太零
- 母上攻略竹影随行
- 娱乐:巨星演员一条舔狗
- 绿意复仇——我的总裁美母安安大小姐
- 学校的英语老师,身材丰满,喜欢穿丝袜的熟女一枚,被学校的喜欢熟女丝袜的体育老师看中...莉莉娅
- 端庄典雅的妈妈佚名
- 孕达快递:被改变常识的熟女人妻们,为了怀孕摇晃着巨乳肥臀渴求快递员的浓精浇灌波波沙
- 逆子难防(母上攻略同人)e21ed2d
- 我和我的母亲(寄印传奇)气功大师
- 四合院:开局获得一象之力青辰乄
- 骗我养初恋儿子,重生另嫁你慌了?小祖宗
- 万神鼎白玉莲子羹
- 仙女座星系松月兔兔
- 离婚后她惊艳世界明婳
- 结婚当天,妻子的白月光跳楼了星河逐梦
- 重生八零:老太太抛子弃女招财猫儿
- 快穿:那个炮灰我穿过顾陌欧司承偶葱
- 婚姻危机四伏张家三姐
- 离婚后,绝美女总裁带娃找上门司徒长卿
- 妄图春华火野兔
- 学霸穿书:重生九零一路发醉栀清酒
- 都市风云乔梁叶心仪易克1
- 可是她撩我啊一生无虞
- 大乾最狂驸马爷半程烟雨
- 傅总别虐了,夫人催你签离婚协议星河
- 桃色仕途请让我火
- 权臣手中白月光炎棠
- 人族镇守使白驹易逝
- 重生官场从阶下囚到封疆大吏笔下不生灰
- 斗破苍穹之无上之境夜雨闻铃0
- 满门反派疯批,唯有师妹逗比未小兮
- 别叫我恶魔栾青峰弈青锋
- 全球文修:我有唐诗三百首!耳东岐
- 离婚后,前妻抛弃白月光哭求原谅夜里的雨
- 被狗皇帝抄家后,我搬空了整个国库念秋安好
- 在日本当猫的日子南瓜夹心
- 原来我是网球世界的NPC坞伶羽
- 这篇都市文的打开方式不对蒜蓉粉丝蒸生蚝
- 成人礼小努力电话手表
- 不许装乖[电竞]路回清野
- 换脸复仇!京圈大佬都成狗慢慢蓝
- 声优变身系统痛感迟钝
- 独秀江月年年
- 阴郁炮灰吃瓜后被读心七月游云
- 翻垃圾造就人生巅峰[无限]月上汤圆儿
- 高岭神君学会偷窥之后青溪漱月
- 仙女座星系松月兔兔
- 卧底宠妃(高h)晚风情
- 夏天到了少吃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