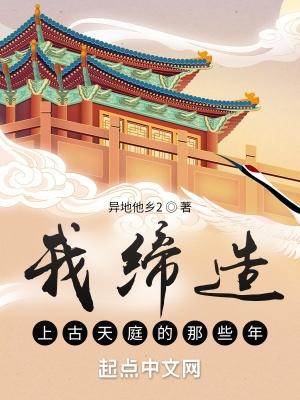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欠债了(第2页)
这也是个叫师父养得很有些天真的和尚,不过人家现已被派出门历练了,这才是正理啊……
姚如意有些黯然地点点头,又接着询问道:“真是对不住啊小师父,我家并非刻意拖欠利钱,先前我阿爷中风病倒了,躺了近一月,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,谁知前阵子取暖时我爷孙俩又不慎叫煤烟熏倒,又将养了半月才算好起来,这才耽搁了还账的事……你方才说欠了多少钱?你与我核算核算,若是钱银数额无误,我这便去取来。”
无畔一听更露出些尴尬。
他头一回出来催债,自然想着要装得凶狠些,才不会叫人戏耍小看,但……早知这姚家过得这么凄然,方才他便小声些拍门了,如今倒显得他有些无礼……
不过同情归同情,钱还是要的,否则回去师父可饶不了他。
他忙从怀里掏出个油津津的红印文书来:“我师父说了,仨月利钱加罚息共三十五贯。
这是当初你家与寺里签的质押契书,你且看看,我们出家人不打诳语,这白纸黑字都写着的。”
姚如意接过来一看,傻眼了。
上面写着姚家这间坐落在国子监后巷的小破宅子,当初竟然贷了一千一百四十余贯的房贷!
且这宅子还是和别家合买的。
房契上写得很清楚,这宅子原本是三进大宅,故主是个权贵,犯罪抄家后,房宅便被劈做两户分别出售。
前头两进被姚爷爷的前同僚林逐买了,姚家花了一千多贯拥有的仅是后罩房兼后院那一进。
位置虽不错,但老旧得很。
难怪姚如意总觉着屋子后头那堵墙砖色新一些,原是隔断林姚两家的界墙——不是,这样的老破小都要一千多贯??
这什么房价,也忒高了!
不过仔细想想也是,姚家买的这三分之一宅,类比起来大概是……后世首都中心紧挨着北大附小附中和北大本校的学区房……忽然又释然了。
至于契书里和姚家合买房子的林家,原主记忆里似乎也有点印象,那林逐原本是国子监的主事,还是姚爷爷这暴脾气为数不多的忘年交,他有个儿子唤林闻安,小时便由姚爷爷启蒙教导,是个远近闻名的天才神童,十七岁便登进士第,拜为东宫侍读,前途无量。
因“教出个十七岁进士”
的关系,姚爷爷当初也是声名远播,不少人来求他指点学问,林家人与其他国子监门生也都时常出入姚家,似乎就成了被邓家用来攻讦原主的那些个“外男”
。
不过隔壁此时并没人在家。
原主混乱的记忆中很多次都出现过姚爷爷为林闻安的叹息难过。
原来这个天才已如流星陨落,他曾被书里潦草提过一嘴的宫变中遭晋王叛党搜捕入狱饱受酷刑,据传伤得极重,几乎到了不能起身的地步,因他家乡抚州的气候温暖舒适些,林逐前些年便辞官带妻儿回乡养伤去了。
他家离开前将钥匙留给姚爷爷,还托他帮忙看顾宅子。
不过这不重要。
这些属于原主的记忆碎片不受控制地在姚如意脑海中一闪而过,又渐渐深埋。
弄清自家欠了多少钱后,姚如意反倒安定了。
她仔细询问无畔每月要还多少债务,无畔一时答不上来,又慌张地翻找他师父给他准备那本催账册子,最后磕磕绊绊地和姚如意说了一大堆,把她绕得云里雾里,只能不断追问。
艰难地谈了约莫两刻钟,姚如意终于闹明白了——姚家与兴国寺是“约期贷金”
,类似后世银行等额本息的贷款方式。
这一千一百余贯钱里,姚家其实只和兴国寺借了八百贯不到,但年利率有百分之五,与寺庙约定好了十五年内还清,所以连本带息一共就有一千一百多贯,如今姚家已偿还八年。
姚如意还仗着无畔年纪轻,旁敲侧击地打探了一下姚家这穷得裤穿洞的,怎么能贷那么多钱出来?还有,这兴国寺怎么跟大财主似的那么有钱,寺庙做这种长期贷款生意都不怕姚家跑路吗?
“先前姚大人乃国子监祭酒,又有多位大人为其作保,还有房契抵押,自然能贷出大额银钱来。”
无畔脸皮薄,说着说着便红了脸。
姚如意听懂了,要是现在的姚爷爷去贷款,人家指定不贷给他了。
看来此时的寺庙贷款也有还款能力背调的。
- 官路之谁与争锋卷帘西风666
- 至尊鼎老狐
- 雪意昭昭七颗荔枝
- 只有鱼知道水陆青栖
- 快穿好孕,美人多子多福涿玉
- 癌症晚期,前任女友疯狂报复我半城清梦
- 上门龙婿叶公子
- 迟音(1v1)唯雾
- 咸鱼世子妃如满月
- 嫁督主锦一
- 穿越影视万界之征服壹樂
- 官途危情巴山破晓
- 无限之禽兽修仙者(修仙少年的艳途)三年又三年
- 官途美人伴赵小二
- 千亿总裁宠妻成狂古凌菲
- 重生少年猎美三年又三年
- 妙手龙医金佛
- 关于我的冷艳警花美母,娇憨开放的妻子,温柔的教师姐姐,和俏寡妇护士丈母娘被我推入深渊这档事何处染尘埃
- 刘志中卢玉清官婿美人香
- 锁春宵,我把太子殿下拉下神坛蒜香烤蘑菇
- 修道十年,徒儿你该下山成亲了青衫剑客
- 造化血狱体甫昔少年郎
- 抗战:黄埔签到百天统领北洋军阀工地一姐
- 天兽鼎妖夜
- 美母为妻带刀侍卫
- 冷酷教师妈妈才不会成为性奴aa19960520
- 美妇厨房(纯爱加料版)kasya10
- 贯穿绿母癖男孩青春期的风骚熟母乱交史云茗的二号机
- 神级反派野山黑猪
- 我的教师美母原来可以这么骚青魔冷枪
- 恶魔大导演娱乐圈老司机
- 斗罗大陆修炼纯肉神梦斗灵
- 斗破之淫荡任务星心
- 高中三年,我让陪读母亲陪我上床两面三刀
- 养成-母子逆推佚名
- 将诸天踩下脚下的淫熟雌菩萨,被巨根正太肏翻匍匐在地脑姦灌精无限
- 冷艳高挑的教师美母hhkdesu
- 重生之娱乐圈大导演开飞机抓仙女
- 娱乐:巨星演员一条舔狗
- 影综:人生重开模拟器娱乐圈老司机
- 高贵神秘的黑夜女神被污秽信仰污染扭曲变成淫贱爆乳,觉醒受虐癖被恶魔鸡巴肏成淫荡母畜紫汵倾雪
- 掌中的美母幕卷
- 妈妈陪读又陪睡佚名
- 被黑人用外星人科技洗脑改造恶堕的居间惠和丽娜愛と税のために
- 肥宅肏穿斗罗大陆清酒
- 我的美母教师纳兰公瑾狼太郎
- 学校的英语老师,身材丰满,喜欢穿丝袜的熟女一枚,被学校的喜欢熟女丝袜的体育老师看中...莉莉娅
- 催眠之御姐熟妇让我操(控制)华风
- 智娶美母纯绿不两立
- 斗破苍穹之后宫黑人恶堕闷三儿
- 穿书七零:带着废物金手指也躺赢了hiro
- 带娃守活寡四年,他衣锦还乡了桔子阿宝
- 刚穿越就成了亡国公主枳静
- 异世界中餐馆糖霜有毒
- 不要慌,先把圣母扔出去!乾离
- 魏尔伦的兰波小姐拯救计划Bladeren
- 五星人才!这员工我招定了!东风胡
- 骂谁害群之马呢,叫我警神河北赵子龙
- 温顺小娇妻,离婚后一身反骨一群秀秀
- 天王归来在都市飞翔人骆驼2
- 神豪:开局日入一万块棉小城
- 朕是暴君也敢造反?送他轮回晕奶
- 大明:孙儿雄英请皇奶奶登基佛系无忧
- 槐夏悠氧
- 武者世界,你怎么教人修仙爽文快刀手
- 醉仙葫盛世周公
- 分手当天去相亲,前任狠狠破防黄油椰卷卷
- 寡夫回忆录粥小啾啾
- 模拟千万次,一身金色天赋怎么输弹珠汽水
- 她年会喝醉,敲开霍总房门爆款糖糖
- 龙潜苍穹八月初八
- 医仙临都人生几渡
- 逍遥小刁民三月生
- 神明,但十级社恐[西幻]鹤梓
- 一天一抽奖,把自己抽成魔女梦里寻九
- 跑路后被疯批男主抓回成亲南隍如钩
- 小陆大人他言而无信闻希
- [hp]命运交织阿竺快去睡觉
- 黑化暂停,先给老婆买冰淇淋林沐彤
- 白切黑反派又装乖演我夜饮三大白
- 攻略疯批男主后他彻底黑化了南隍如钩
- [红楼]怨偶双重生青青小艾
- 偷偷暗恋我的角名同学你问我吗
- 他的手段蝗蝗啊
- 社畜也能成为魔法少女吗卢贝多
- 横刀夺穗度明木
- 姐姐不说话(骨科)不相逢
- 团宠三岁小皇孙吾彩
- 六零美人,靠爷奶粉爆红诸葛扇
- 马甲拒绝为苏格兰去死灼东云